摘要: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Гумилёв)是俄国阿克梅派诗人的领军者。诗人一进军俄国诗坛,便以“征服者”的形象出现在其中。在古米廖夫的诗歌创作中,非洲、西亚、北欧、甚至中国都是诗人创作灵感的来源,俄罗斯之外的主题和意象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本文按照古米廖夫创作时间顺序,分析诗人创作前期、中期、后期的部分诗作,略谈古米廖夫欲征服的几个方面,并在后殖民主义视域下分析诗歌中外国主题意象,进而得出尼古拉·古米廖夫因自我中心主义性格和固有的弥赛亚意识,因此在不同创作时期均以“征服者”这一形象存在于世界诗坛中的结论。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1886-1921)是阿克梅派创始人,在他不到二十年的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与大多数俄国诗人相比,古米廖夫的诗歌里写历史多于写现实,写外国多于写俄国。杨开显指出,古米廖夫性格执着,勇敢坚定,颇为自信和自负,喜欢扮演征服者的角色。因此,他是作为征服者的歌手而登上俄罗斯诗坛的。他向往航海、探险、向往到异国旅游和建功立业,几次深入非洲腹地,不畏艰辛,探险猎奇;又勇敢地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英勇杀敌,建立功勋。所以,他的诗歌既呈现出绚丽的异国风情和对异国土地的思念(他是第一个把奇特的非洲风情写进俄罗斯诗歌的诗人),也表现出战争中的英雄情怀和战争的残酷及不人道的一面。(古米廖夫20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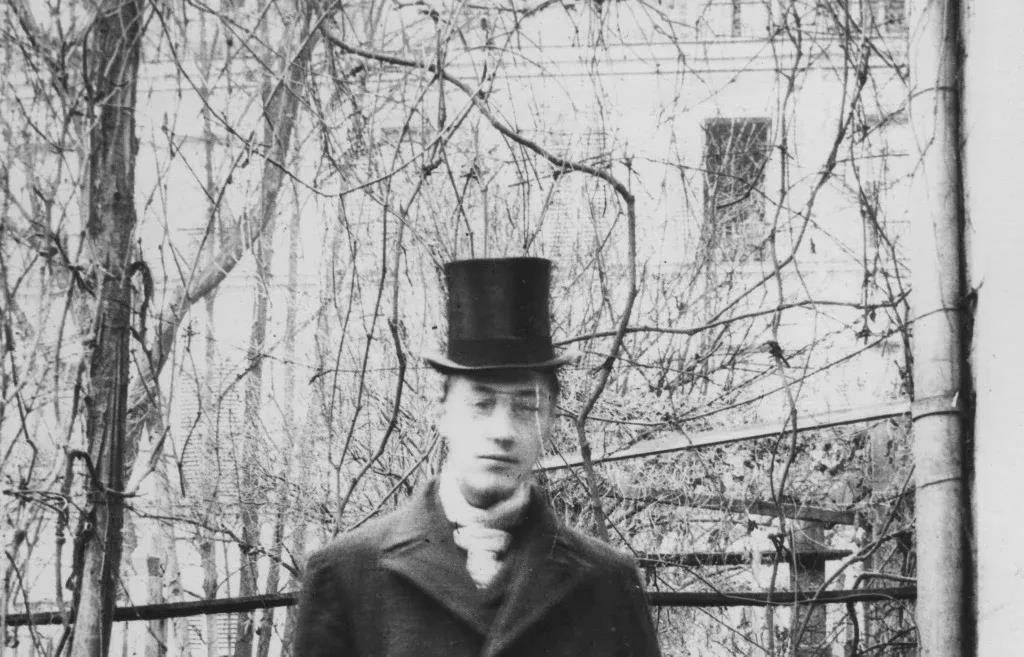
纵观古米廖夫的创作生涯,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其所处的流派更迭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从1902年诗人创作生涯的开始,一直到1910年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完婚为止;第二个阶段始于1910年古米廖夫出版自己的第三部诗集《珍珠》,止于1918年古米廖夫从前线经法国返俄,并与阿赫玛托娃离婚为止,此时阿克梅派的活动基本已经停止,仅剩下诗人们小范围的联系;第三个阶段始于同阿赫玛托娃离婚,止于1921年古米廖夫被处死。我们可以概括为年少成名的少年古米廖夫、血气方刚的青年古米廖夫和提前进入中年危机的中年古米廖夫。回首古米廖夫创作生涯的始终,不难发现“征服者”的形象出现在其创作生涯的各个阶段。古米廖夫第一部出版的诗集即叫《征服者之路》,“征服者”、“探险家”的形象出现在诗歌中;而在诗人生前最后一年出版的诗集《帐幕》中,非洲主题贯穿了整部诗集,诗人用大量篇幅描写了红海、埃及、撒哈拉、苏伊士运河等非洲的风土人情。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探寻古米廖夫少年、青年、中年三个创作阶段的殖民主义色彩。
笔者认为,从1902年诗人创作生涯的开始,一直到1910年与·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完婚为止是古米廖夫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在此期间,古米廖夫深受象征派诗人的影响,并努力探索新的诗歌真理,努力追求打破象征派的局限。早在1902年,古米廖夫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我从城市逃向森林》:
我从人群逃向隐居之地……(Гумилёв2015:309,译文为笔者自译,下同)
在诗集《征服者之路》中,《歌手与国王之歌》无疑是最能体现古米廖夫拥有王侯将相般灵魂以及敢于探寻猎奇的灵魂的诗作。全诗通过描述一个歌手在国王面前口出狂语,国王无法忍受将歌手杀掉的故事:
我不愿再长时间地听疯子说话,
我举起了闪闪发光的宝剑,
我赠给歌手一朵染血的鲜花
以奖励他粗鲁无礼的话语。
……
如同原先在烟雾弥漫中看不见光亮,
如同原先特罗利浪迹江湖,
他这个可怜的人害怕宝剑,
不知道威严的国王在号啕痛哭……(Гумилёв2015:43)
如身着钢铁铠甲的征服者,
我从家中出门,欢快地行走,
时而在快乐的花园中休憩,
时而被引向深不见底的鸿沟……(Гумилёв2015:43)
古米廖夫崇高的梦想流露于这首诗中,曾思艺认为这是一种少年男性渴望征服、向往建功立业的浪漫激情,一种少年式的渴望探索未知、神秘、进行冒险的浪漫激情。(曾思艺2016:342)古米廖夫的激情,是典型的斯拉夫主义者的浪漫激情。古米廖夫受十九世纪斯拉夫主义者思潮的影响,在少年古米廖夫心中,他与他的祖国必然承担起拯救欧洲乃至全世界普世的,具有弥赛亚主义的使命。少年诗人的心灵仿佛如哥萨克自由的骑兵,展现着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两极性和矛盾性。少年时代的征服者形象必然为诗人之后具有“征服者形象”的创作埋下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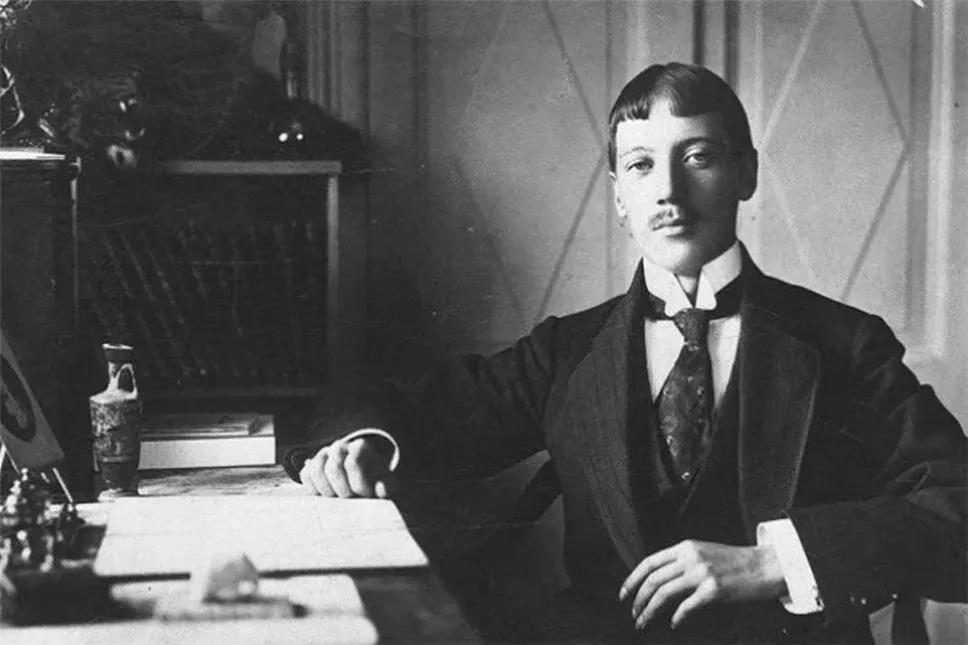
1910年,古米廖夫同女诗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完婚,古米廖夫的少年时代已经过去,新的创作阶段已然开始。同年古米廖夫出版了自己的第三部诗集《珍珠》,这本诗集是古米廖夫的成名作。勃留索夫认为古米廖夫在这部诗集中创造了一些国度,诗人自己创造的生灵在其中按照诗人自己的意念生活着。在这部诗集中,古米廖夫在异国他乡、在神话中以征服者的姿态探索世界。《在旅途中》一诗中,古米廖夫明确宣告称,即使在旅途中有群山昏暗的影子,即使面对悬崖峭壁,面对死神一般可怕的蛟龙,也绝不会调转前进的方向。即使往日如金子一般,一无所有的现在是更好的:
终年常绿的花园寻到。(Гумилёв2015:82)
古米廖夫在1916~1918年多次驻留巴黎。随着战争的豪勇退去,古米廖夫“征服者”的思想似乎安分了一些,古米廖夫重新在巴黎——这个到处都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多彩之地找寻创作的激情,并以“征服者”的形象猛然追求一个法俄混血姑娘叶莲娜。一切的美好光景似乎在1918年结束,阿克梅派诗人的活动已然绝迹,古米廖夫也在1918年收到阿赫玛托娃要求离婚的信,古米廖夫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也结束了。

当我的生命休止之时
在《火柱》中,征服者的形象已然不多见,古米廖夫似乎预见到了自己的不幸,征服者的形象慢慢隐藏,进而消失。古米廖夫后期殖民主义色彩的淡化和消失一方面是诗人的迷惑和绝望,另一方面与阿克梅诗派的衰落有关。阿克梅主义者思考的不是现实社会的矛盾——即诗歌的主题内容,而是高超的创作技艺——即诗歌创作的形式。张建华指出,阿克梅派诗人只是驻足于实际上是自己编织的人造臆想的“物质世界”,从唯美主义观点出发来理解“人世”,主张通过对人的意志、本能的启迪使人逐渐“完善”。所以,他们幻想出的原始自然的、安谧静止的“现实”世界,最终不能不呈现出虚伪现实主义的色彩。(张建华2012:69)古米廖夫显然在最后的创作生涯中意识到了阿克梅主义的局限性,古米廖夫一生追求的“征服者”形象,随着阿克梅主义诗歌理论被怀疑而土崩瓦解。
“征服者”形象的生成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诗人勇于探索,不畏危险,勇于挑战、自我中心主义的性格,古米廖夫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时刻认为自己是诗坛的主导者;其二是俄罗斯思想中的领土扩张意识、弥赛亚意识、普世主义思想造就了古米廖夫的“征服者“形象。但同俄国殖民主义的局限性一样,古米廖夫诗歌创作中的殖民主义色彩也具有类似的局限性。诗人创作中的殖民主义衰落的原因也有两个,外在原因是十月革命后,古米廖夫深刻地感受到人生的危机,诗人对眼前所发生的革命、对生活意义和人生道路寻求充满迷惑、恐惧和绝望,自然便收起了“征服者”的形象;而内在原因是古米廖夫意识到阿克梅主义的局限性与阿克梅诗派的衰落,阿克梅主义者们幻想出的原始自然的、安谧静止的“现实”世界,最终不能不呈现出虚伪现实主义的色彩,古米廖夫觉察到了这一点,他高调的“征服者”形象自然就不堪一击,“征服者”形象在诗人创作的后期也就销声匿迹了。
首都师范大学张政硕
- Номинальный и реальный эффективный обменный курс Китая продолжал сокращаться в июне
- В Пекине выпущены памятные конверты, посвященные 70-летию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ип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 Б. Джонсон вступил в должность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 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умынии произошли важные назначения
- Ливийцы должны играть ведущую роль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в Ливии -- китай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
- В первом полугодии отмечен 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рост импорта в сфере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ой электрон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Китая
- Цветущие поля рапса в провинции Цинхай
- Китай обещает снисхождение к беглым преступникам, сдавшимся в руки правосудия
- Красноярск готовится к проведению знаменитого гулидовского турнира по дзюдо «RUSSIAN JUDO TOUR»
- В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е состоялся II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форум по селекции и технологиям возделывания сои
- В Ичуне стартовал культурный фестиваль «Красная сосна» (Хунсун)
- Третий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й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ый фестиваль стартовал в Суйфэньхэ
- В Харбине стартова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нкурс струнных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 имени Алисы и Элеоноры Шенфельд-2025
- В Беларуси реальные денежные доходы населения за пять месяцев с начала 2025 года выросли на 10,5 проц. -- Белстат
- Евросоюз не смог одобрить новый пакет санкций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 В первом полугодии этого года в Китае наблюдался стабильный рост добычи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